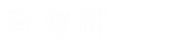外星人很有可能就生活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又如何去发现他们呢?
17世纪70年代末期,荷兰科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通过显微镜观察一滴水时发现了一个世界。这是个微小的、蠕动的世界,充满了奇怪物类。它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却不为人所知。在当时的人看来,人类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和目的,这些微动物无论可见还是不可见,对我们的存在没有影响。那么它们为什么存在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微动物是微生物,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它们使我们生病、使我们健康、分解我们的垃圾、喂养我们食物链的底层物种,并且为我们制造氧气。人类对微生物的无知并不影响它们的重要性,就像苹果砸到艾萨克·牛顿头上之前重力也非常重要一样。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及其研究工具
现在,我们可能处于另一个类似的哲学悬崖,将发现藏匿于我们世界中的第二个重要世界,即地球上的外星生命。如今,科学家在土卫二冰冷的间歇泉以及木卫二冰壳下的海洋中寻找外星微生物,在火星上寻找生命曾经存在过的线索,用望远镜观测遥远的外行星的大气层,试图发现生命的迹象。但或许这些努力都是舍近求远。如果地球上有多条生命线且与我们的祖先分开进化,那么我们不用离开地球就能发现外星生物。
这些“外星人”(指上文的“外星生物”)的后代可能仍然生活在地球上,与列文虎克发现的细菌一起蠕动着。科学家将这些假想的伴生物称为“影子生物圈”。如果发现一个影子生物圈,就能证明生命不止发生过一次。如果生命可以在一个星球上发生两次,那么它必定在无数的其他星球上发生过无数次。但是要发现一个影子生物圈,我们的多数科学方法都无能为力。影子生物圈的提出者也是其最大的支持者卡罗尔·克莱兰德说,这是个问题。

克莱兰德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哲学家,当她在西班牙的天体生物学中心度公休年假时,产生了上述想法。当时,克莱兰德在调研那些研究微生物的科学家。
克莱兰德问道:“如果你们有一个土壤样本,怎么识别里面有什么?”科学家会马上给出通常的答案:将样本置于显微镜下,放入培养皿中,制作数百万个DNA拷贝,将基因编目。这种方法假定所有微生物都拥有遗传物质,其遗传方式跟人类遗传物质的遗传方式一样。但这种习惯做法令克莱兰德不安。她说:“除了那些与熟知的地球生命几乎相同的东西外,你们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发现别的东西。”克莱兰德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地球上不止一次产生过生命?即使可能,用现有的方法也永远不可能检测到来自第二(或第三)次生命诞生的生物体,因为我们的检测只能测到熟悉的生命。“但是这些生物体如果存在,应该在环境中留下痕迹。”克莱兰德说。
2007年,克莱兰德在《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历史与哲学研究》杂志撰文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痕迹:沙漠漆皮。它是一种漆状薄膜,覆盖在地球上荒漠地区的岩石上。从利比亚的阿兹兹亚沙漠到南极的干谷,都能见到岩石上的这种微薄的沙漠漆皮。几千年来,人们通过刮掉漆皮制作岩画。沙漠漆皮层层出现,但每1000年,其厚度只增加人类一根头发的直径。沙漠漆皮中有丰富的砷、铁和锰,而其覆盖的岩石中没有这些元素。没有已知的地球化学过程或生物过程能够解释其成分,但沙漠漆皮实实在在地存在。因为这些发现,克莱兰德呼吁科学家不要低估像沙漠漆皮这样的异常现象,应该去探究这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东西,因为它们或许就是格格不入。
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奇异生物体,在技术上可以称作“熟知生命”。说它们“熟知”是因为它们的确遵从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即解释基因信息在一个生物系统中流动的法则。耐毒性生物可在核废料中生存;嗜酸生物可在电瓶水中生存;需氧生物一旦无氧即死亡;嗜热微生物在海洋深处的热液喷口茁壮生长。就像电影《侏罗纪公园》所说,生命总能找到出路。原文地址:http://www.UFO-1.cn/plus/view.php?aid=1138
然而,即使发现最熟知的生命形式也并非易事。根据最新的估计,目前我们只发现了地球上14%的遵从生物法则的物种,其中只有1%我们能使其在实验室里生长。影子生物圈或许能使我们了解其中的缘由。克莱兰德与天体生物学家谢莉·科普利(也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工作)合作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地球上替代性微生物生命的可能性》。她在文中说:“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生命间至少略有不同,但我们不知道不同到什么程度。”就像锤子和长柄大锤都能用来钉钉子一样,其他化学组合也可以使生物体生长、适应、回应刺激以及再生,即生物体生存。那么,是哪些化学物呢?又是如何组合的呢?要理解这些需要追溯到生命的起源。

如查尔斯·达尔文所言,地球上的生命或许起源于一个“温暖的小池塘”,或许起源于海底热液喷口,又或许来自一个火星陨石,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地球形成5亿年后,分子开始自我复制。许多科学家相信,第一种自我复制的分子是RNA(核糖核酸),即基因生命的最初形式。这个RNA世界演变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地方,在这里出现了DNA和蛋白质。其他科学家则认为,一长串纯化学反应不断释放出复杂的有机分子,之后这些分子加快了反应速度并产生了更多的有机分子。经过许多轮这样的新陈代谢,产生了遗传成分,最终产生了基因。
在那些散布在海底热液喷口周围不为人知的古老生物体内,或许仍然隐藏着不同顺序的字母组合。
DNA是所有起源故事的最终结论。DNA有三个部分:被称为脱氧核糖的糖、磷酸盐分子和某种核酸碱基,即腺嘌呤、蓝色素、鸟嘌呤和胸腺嘧啶当中的一种(在RNA中,尿嘧啶代替了胸腺嘧啶)。但是六种碱基是自然产生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生物设计师约翰·查伯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分子是否可以做到DNA能做到的。在那些散布在海底热液喷口周围不为人知的古老生物体内,或许仍然隐藏着不同顺序的字母组合。

DNA不是其他生命唯一偏离熟知生命发生化学演变之处。DNA指导我们的身体产生某些特定的蛋白质,即20种不同氨基酸的聚集物。在实验室里,有了正确的起始原料和紫外线的帮助,氨基酸会自然聚集。氨基酸也覆盖在彗星表面,其构件在星际空间漫无目的地飘荡,自由自在,并且非常丰富,现在有100个。影子生物可能有80个额外选择。
即使我们的DNA使用同样的氨基酸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形状。如果你在实验室里制作氨基酸和脱氧核糖,你会得到两种镜像,被称为“左撇子”和“右撇子”。但是在生物体内,你只能发现左旋氨基酸和右旋糖(即葡萄糖)。影子生命可以是灵巧的,或是规则生命的镜像,其分子可以像Photoshop那样迅速翻转。天文学家迪米塔尔·萨塞洛夫和遗传学家乔治·切奇是哈佛生命起源倡议计划的科学家,他们想制造一个类似的镜像世界的生物体。他们希望他们制造的微生物某一天会生病。“如果那里存在右撇子生命形式,其中必定有许多是病毒,这些病毒将试图劫持我们制造的仿生细胞的DNA。”萨塞洛夫于2013年对《卫报》这样说道。如果病毒攻击,我们将知道病毒的存在;如果病毒存在,它们的一些猎物必然存在于哈佛实验室以外,而且早在哈佛及其实验室存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让科学家去发现影子生物圈就好比要求黑猩猩为汽车加油,他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或用什么工具。不过,莱兰德对此提出了建议——在生命“不应该”存在的地方寻找生命。即使是最耐热细菌,即超嗜热菌,在122℃以上也会死亡。如果你发现有东西在150℃的环境下生存,那么它们很有可能不是我们的同类。乘气球进入高空大气层,爬上高原,乘雪车去南极,驾路虎汽车去阿塔卡马沙漠,穿上“世界末日西装”冒险进入铀矿,然后保持警惕,注意那些能使我们说“哈!奇怪!”的现象,而不是那些让我们说“啊,找到了!”的现象。之后仔细考虑对它们的解释,那或许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另一个类似沙漠漆皮的神秘发现涉及多余气体。如果我们统计所有生物释放出来的碳,然后对比大气中可发现的碳,两者不相称:空气中的碳比“应该”存在的碳多出5%。或许多出来的碳来自影子生物的排泄物,而我们没有计算在内,或许不是。或许我们已经发现了影子生物——某些在实验室里不再生的害羞且倔强的微生物,而那些实验室是科学家为遵从法则的生命建造的温床。也许影子生物只是沉默,而我们应该努力探寻。

如果我们只是寻找已知的生命,那么我们要找的都已全部找到了。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系统的影子生命寻找计划。但早在2010年,天体生物学家弗利萨·沃尔夫·西蒙领衔的团队就在北加利福尼亚莫诺湖的咸、碱、砷饱和水中寻找怪异生命。在那里,沃尔夫·西蒙的团队发现了一种被称作GFAJ-1的生物。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的DNA中都有磷。当该团队将GFAJ-1去除磷时,GFAJ-1似乎用砷替代了磷。这种替代是致命的,会杀死你体内的细胞,因为尽管在元素周期表中两者有“兄弟般”的特质,但其相似度还是不够高。然而,GFAJ-1用砷替代磷之后好像也存活得蛮好。尽管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影子生物,但这似乎至少进了一步: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熟知生命可以有影子生命一样的行为。

该团队向《科学》杂志投了一篇论文,美国航空航天局马上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但是当其他科学家未能复制这一研究结果时,沃尔夫·西蒙的15分钟演讲很快变得声名狼藉。细菌确实在砷浴中生存,但是它们仍然需要使用磷。就像一个西伯利亚隐士仍然是人一样,GFAJ-1还是常规生命。该团队的思想或许过于开放,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寻找已知的生命,那么我们要找的都已全部找到了。
我们不了解的生命发现暗示,生物学就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是一种普遍规律。如果你从一个地面建筑上扔出一把长号,它会掉到地上——每次都这样。如果分子云有合适的浓度、动力和成分,它们会塌缩成新的恒星——每次都这样。如果它们塌缩成新恒星,残余的气尘将总是塌缩成行星。或许行星有合适的成分、合适的温度,它们总能产生生命。影子生物圈表明生物的出现是合适条件作用下的正常结果,而不是一个神秘的彩票现象。
1670年,当范·列文虎克观察无形的微生物世界时,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观点:微生物世界太小,没法观察。现在,不是微生物世界的存在,而是新近发现的微生物世界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动摇着人类的宝座。
今天,如果问在合适的条件下生命是否会复制自己,许多人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是,如果说人类是某个预见性法则的可预见结果,其具体和复杂的证据会彻底动摇人类的宝座。